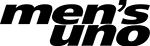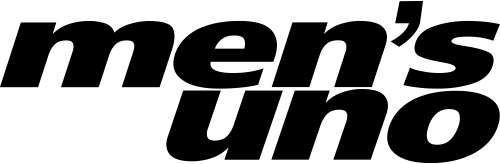m: 你對「模糊」是如何定義的?
Y: 這個詞很新穎,這也是一種身分象徵,如民族、宗教一樣,可分門別類,亦可引起紛爭。
m: �你是否將模糊作為設計概念?
Y: 大概下次吧?
m: 比起設計師,你更願意稱呼自己為裁縫,你認為這二者之間最根本的差異是甚麼?你拒絕以創意總監自居的理由是甚麼?
Y: �倘若我以創意總監自居的話,那必須是艱辛的,必須是關於時尚的,而且還得考慮這個角色的種種。但如果我是一位做衣服的人的話,我不必為主流時尚工作,而選擇範圍變得更寬廣。
m: �既然做時裝,就會有明顯的季節性和潮流性,一年發佈兩個系列,每個系列都要被賦予一定的主題,從裁縫的角度來看,你怎麼理解這種「始終在變化」的創造?
Y: �有個非常出名的故事:當你向一位藝術家提問,哪一個才是你認為最成功、最喜愛的作品,那麼答案必定是下一個。同時我亦不停地尋找新的製作方式,而製作時裝最有趣之處就是那些不能用筆墨來形容的感覺。那些感覺就像一些圖片,模糊的、迷人的、令人興奮的。每當我遇上那些圖片,我便竭盡所能去追逐它們。
m: 你抗拒主流的潮流,也在不停地尋找新的靈感,這種靈感表達卻也可能成為新的潮流,你是否會因此矛盾困惑?
Y: �我並不關心那些,我所做的是成衣系列,它伴隨著賭博之意。因為我們在不確定訂單的情況下工作,這自然地成為了一場賭博。但經歷過數次這樣的賭博之後,我並不認為我會在下一場輸掉。當我想起那些懂我而又穿著我的衣服的消費者們,我必須繼續。有時候,我希望改變時裝歷史,希望做一些給自己的創作,如果我在製作過程中感到興奮,那便可能是一種創作。另外,時裝是一種團隊工作,包括了各方面的人士,如製版、面料、助手,以及其他專業人士。偶有製版師傅會做出一些意料之外的、迷人的,或令人興奮的衣服。遇上此類事情,我會認為這是上天賜我的禮物。但我必須時刻準備著去捕捉這些從天而降且美麗的意外之物。
m: 在你《做衣服:破壞時尚》一書中,你提到了坂口安吾的一句話:「不表達自我,毋寧死去」,我們很認同設計師有自我立場堅持的做法,時裝就是你自我表達的途徑和武器嗎?
Y: 在我尋找生活態度的過程中,我閱讀了坂口安吾,而我被當中的一些關於藝術家的詞語和句子擊倒了。那些句子大意是「假如你不傾盡所有,你便無法徹底地創新,創意也就到此為止。」若不能創作,我願意奉上生命。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,這也使我發生了些轉變,我喜歡這樣的極端。
m: 你喜歡當代藝術嗎?經常去看展覽嗎?最喜歡的藝術家是誰?
Y: 當代藝術?很抱歉,我不懂任何當代藝術。我常受邀去參觀當代藝術展覽,但我每每到場都是一頭霧水的感覺。至於喜愛的藝術家,有一些,但不好說,這取決於當天的心情。
m: 你將時裝設計視為藝術的一個類別,認為它是一種直觀的藝術表達形式。身為「設計師」,你如何理解繪畫、雕塑以及裝置藝術領域的藝術家?你和他們的異同點在於甚麼?
Y: 我不是一名藝術家,我只是一位做衣服的。衣服不一定是藝術,這根據情況而定。在職業生涯的初期,我並不認為我在搞藝術,那只是在做衣服。一張紙,是二維。它被折曲,成了三維。衣服並非真的三維,而當人們穿起衣服,人們的感知、快樂或悲傷,我認為這些是四維的。有時候,我將一件普通大衣放到模特兒身上,然後在天橋上發表,但我並不會因此而興奮。但同一個人穿著同一件衣服在街上出現,對我而言這是藝術,同時是種驚喜和新的演繹方式。所以這都取決於誰穿、如何穿我的衣服。
m: �你曾經為歌劇設計服裝,也為現代舞設計服裝,甚至還充當音樂人出過唱片,這種身分的切換對你來說,最大的意義是甚麼?
Y: �這是個夢想,每人都有。最重要的一點是人類是自由的,有選擇權的。
m: �你對時裝的熱情會永遠持續下去嗎?想過退休嗎?退休後要做些甚麼?
Y: 我從未想過退休生活,很無趣。我會一直做下去,直到我倒下為止。
TEXT / SHAUN INTERVIEW / 潤